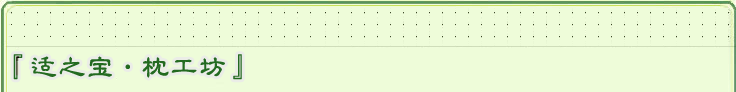好多事情说起来都很麻烦。
不好表达,如果容易表达出来,就很有意思。
当然,都是生活琐事。
是琐事,就得努力让它有趣。
那天,我买了一只枕头,这样,中午躺在凉席上休息的时候可以舒服一些。
直接把脑袋搁凉席上也很舒服,但,它的前提是你没有用过枕头,如果用过了枕头,你就会觉得还是有一只枕头脑袋会感觉更舒服。
麻烦吧。要是没有枕头这种东西,你的脑袋同样会觉得舒服,但是,自从发明了枕头,人们就不想再过没有枕头的生活。这就是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比如,吃生肉,或生吃肉,或者肉生生的吃,也很舒服,可是,因为有个白痴,一般来说,天才在群众眼里都是白痴,有个白痴烧烤了之后,所有的人都骂他白痴,却发现白痴是对的,烧烤了之后肉真的是好吃极了,这样,动物就变成了人。
人与动物的区别正是吃肉的时候烧烤不。可惜,有些现代人返祖,在饭桌上,抓起活蹦乱跳的大虾沾了油盐小料就往嘴里塞。我看到大虾的尾巴还在他的嘴角上摆动,大虾的身子已经半截到了他的肚子里,这时候,我就装着上洗手间走了,吃不下饭,没办法,我觉得我进化得有些问题。
很麻烦吧。
这只枕头不错呵,名字也好听,金谷茶香凉枕。
我仔细看了说明,也就三行字,一行是名字,一行是说百分之百植物纤维,还有一行说的是成份,稻壳和茶梗。这些词汇听上去就很舒服。我就高高兴兴地抱了它回去了,鼓鼓的,外表是竹子绿色,更显得凉爽。
关于凉爽,古话总是说,心静自然凉,其实,这是自我安慰的话。这句话设置了一个常人达不到的标准,同时,心静到什么程度,也没有统一。
既然你觉得还是热,说明你心还是不静。既然你心不静,当然不会感觉到凉爽。比如,一些意识形态的教育,为什么你没有那种大无畏的精神,那种公而忘私,或奋不顾身,或者言行一致的青松品质与红梅风骨,却竟然投降了,是因为你心不静,心一静,一切都在掌握中。
这样看来,主要的问题你就得自责,觉得是自己的卑下和无能导致的热,而不会再埋怨现实生活环境的残酷。不过,如果你做到了心静,其实,还有什么凉的概念存在吗?还有什么热的意义吗?
当我们原谅了自己心不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热的时候,还有凉席和凉枕头这种事情,特别是当我们发现总是谴责我们不够心静的那些人,原来都在空调中,都在冰爽茶中,都在寒冽的清泉中,都在大麻凉席和蚕丝锦被中,过着朱门酒肉的生活,我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就更得原谅自己的心不静了。
为什么你的心不静?
原来是你没有那些凉爽的东西。
回到办公室。
我把凉席铺开,把凉枕头平放在地上,躺下去,呵呵,真是爽呵。
落地窗外,是赤日炎炎,是低沉的七月桑拿天,是车水马龙,是高楼的反光。但,那些热气蒸腾和我无关,我在空调的家里,在凉席上,在稻花香的枕头上。
然而,躺下的时候,就忧从中来,枕头很不舒服,太高了。我拍了拍它,努力把它拍成烧饼,可惜,它还是象一只馒头那样鼓起来。
关于馒头和烧饼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小水车月亮光光发一条短信来,说,最近没有钱了,买不起烧饼吃了,所以,就只好买了一只馒头,把它拍扁了,拍成烧饼的样子吃了。
这个情景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承认,我不是那种特深刻的人,所以,小水车月亮光光发了一个小短信,我就把它当成了深刻的东西珍藏着了。后来,小水车月亮光光去了上海,现在混集在十里洋场,也不知道还有钱买得起烧饼吃不,也可能还是在豫园或者外滩上买个馒头拍成烧饼吃着?
上海,我在1991年的时候去过,低矮的里弄,挤来挤去的豫园,狭窄的南京路,我穿个破运动短裤,红色的,露大腿比较多一些,站在外滩上,歪着脑袋留了个影,身后是大船,还有一张,身后是外滩的大楼。后来,我就在一平板车上,让一个中年人驮着去住店,穿来穿去,往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巷子里钻,再后来,就进了一家旅店,不知道它是几层砖房,反正印象中套来套去都是房间,都是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孩子,哭着的与闹着的,我光着身子躺在竹席上,还是热,就把短裤扔了,还热,就把内裤扔了,从此以后养成了睡觉的时候不穿内裤,醒来的时候,它总是直翘翘的,令我好长时间看不太懂。
我怎么也没有办法把高耸着的金谷茶香凉枕拍成烧饼的样子。
这时候,我就有些愤怒。我愤怒的时候比较多,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祖国总是碰到太多的令人愤怒的事情。
特别是,当我总是用一双简单的、乡下的、缺乏自信的、不敢声张的、前怕虎后怕狼的眼睛望着这个光怪陆离没有规则或者有规则也不遵守的世界,我就觉得悲从中来。这很不好。体检的时候,医生说,你的脾大呵。我说,什么意思。医生说,是不是常常生气呵。我说,没有呵。医生就低头不语,暗自揣磨,为什么这个家伙的脾大呢?
关于悲从中来,我是这样想的。我喜欢那种悲从中来的眼神。那种眼神属于尼古拉斯·凯吉(Nicolas Cage)。以前,我觉得梁朝伟的眼神与尼古拉斯·凯吉的眼神有些像,后来,我看他们的片子多了,就能够进一步把他们眼神的不同分开了。
梁朝伟的眼神是忧郁的,暧昧的,关怀的,很有女人缘的那种眼神,那种眼神更多的是一种关于两性的淡淡的愁绪,然而,尼古拉斯·凯吉的眼神是人文情怀的,是切近人生的,是普世的,是那种生活怎么能让它这样过的眼神,是觉得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情,是认为如果他来到这个世界看到了那些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他不改变点东西的话,简直就是没有天理与王法,简直他就不应该生在这个世界上,简直就应当是人与神加上鬼都要出离愤怒的事情。为什么是人神共愤?把鬼忘了吗?
当然,这种人文情怀在王小波的眼神中也有,不过,王小波的眼神表达的直接就是战斗,是那种愣头青,是那种我是二百五我怕谁,是那种无所谓畏惧,是那种看不怪就很不舒服,是很不舒服就要战斗,至于这种战斗是直接拿枪还是间接拿笔,那只是战斗的方式,但,王小波的眼神显然是战斗的。我也想在王小波的闪闪红星照耀下去战斗,后来发现天生就不是那种大手一挥应者就云集的人,也就是说,天生就是贱人,所以,就黯然神伤,低下了头如一条狗似的活着了。
尼古拉斯·凯吉总是那种悲从中来的味道。我看过的一部片子忘了名字,是北大的小录像厅看的,那时候,我没有事情可做,就跑到北大的小录像厅看最新的录像片,尼古拉斯·凯吉偶然撞上了一个电视镜头,镜头里表演的是杀入游戏,一个屠夫把一个女孩生生地杀掉,表演给一些富得流油之后的人看。
开始,尼古拉斯·凯吉以为只是游戏表演,后来,他觉得味道不对,似乎真的是在杀人,因为,有些人很有钱,很有钱之后就很变态,很变态就玩到了杀真人玩的地步。尼古拉斯·凯吉瞪着一双忧郁的眼睛,就着手调查这件事。
你管人家呢,你又不是警察,但,尼古拉斯·凯吉不管不顾,他非要弄清楚不可,结果,就把这件事搞得水落石出,把这种罪恶暴露于天下。
然后,尼古拉斯·凯吉在危险中悄然而又忧郁地离去。
我有些愤怒,却不是太愤怒,有些忧郁,却不是太忧郁,毕竟,它只是一只金黄金香蒲绒枕头,毕竟,它只是一只过于饱满的凉枕。
当时,我躺下后,辗转反侧,睡不踏实,暗自发狠,觉得,为什么那些做枕头的人,做好以后不试试它能不能让人睡安稳呢?至少保守地做的话,也是应该把枕头做到中等程度的高度,如果人们觉得它低了,就把里面的内容挤在一起,如果觉得它高了,就把里面的内容平铺开,不是就能够相对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了?
关于满足人们需求的事情,我还有很多想法。
比如,在学校读书,都是双层床,都是木板加铁板,上两层床的梯子有棱有角,椅子也是方方正正,硬板一块。我到过好多宿舍,因为,我读过好多年的书。读书多的人很没有用。我就是为?作个没有用的人才来到这个人世间读书的。
在各种宿舍里,我几乎很少看到有哪位同学会喜欢坐学校给他们配备好的椅子,他们总要把那些椅子扔在一边,因为它们根本不能长期坐下去,然后,自己破费买别的软椅子。
上帝看在眼里呵,你知道吗,写论文,看书,上网,要整天整天地呆在桌子前,那些鬼东西做的桌子与椅子与床,硬梆梆的,老来粗糙的肌骨都受不了,更不要说那些稚嫩的年轻的肉体。
当然,人家也说过,古人还头悬梁锥刺骨还卧薪尝胆故意找不舒服呢,看你做什么了,没有志向的人总想着那些舒服的事情,有志向的人从来都是活在地狱中找机会努力煎熬自己。
一想到这样来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就觉得数天下的农民工最幸福,原来他们都是在卧薪尝胆,都是在磨刀霍霍要砍柴,都是抱着远大的理想,都是为了将来的舒服而忍受今天的不幸。
这样想下去的话,我就会开始怀疑,还要不要一看到可怜的人就扔几个铜板,或者,还要不要再给地震灾区的人们捐款捐物,还要不要当一个抱孩子的女人站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立即起来,不管自己有多累,加了几个小时的班,一定要把座位让给她们?
我觉得得把枕头加工一下。
就把金黄金香蒲绒枕头拿回家去。
回家的路比较远,它得和我一起乘坐地铁。全世界人民运动会来了,人比较多,不是人都来了,是对私家车有了适度的管制,所以,地铁的人多了。它得和我一起挤。它鼓鼓囊囊地和我一起回家。
那天暴雨如注。
我在小区的门口没有看到那个中年女裁缝。我以为也是让警察抓去拘留一周了。这条小街最近被拘留的人多了,卖安徽板面的,卖烧饼羊肉串的,卖麻辣烫的,卖咸鸭蛋的,卖桃子李子的,卖西红柿青椒的,不少人都有了人生中的拘留经历。
这要你怎么看。
我不饿的时候,走过这条繁花的小街,就觉得真是人山人海,乱七八糟,又脏又杂,很得治理整顿一番,但是,当我饥肠漉漉的时候,就觉得那些麻辣烫,那些烧饼,真是又香又脆,或者,当我想自己动手做点吃的时候,就觉得那些卖菜的,那些卖鸡蛋的,那些卖凉菜的,真是方便极了,这些普通的小买卖人真好,天南海北来到这条小街,满足大家的各种生活需要。这时候,我就会恨那些警察,厌恶那些城管,觉得他们都是牲口畜类。
可是,这些城管和警察也没有办法,也得受委屈,这就象咱自己家过年的时候来个客人走亲威,总也得粉饰一下房里内外,都牺牲一下吧。
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全世界人民运动会和他没有什么屁关系,所以,就不听话,三令五申不听话,政府就急了,政府一急,就得动用合法的武装暴力,都动用,民主国家都动用,更不要说咱法治(?)国家,所以,就有不少人去拘留所了。
有个卖板面的安徽女人,从来不知道监狱、开守所以及拘留所的区别,所以,我们在她的小店吃面的时候,她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说她刚从监狱出来,哎呀,住了一周呵,天哪,丑死我了,长这么大,竟然进了监狱,我只是个卖安徽板面的,一碗才三块五呵。
我就只好笑笑,安慰她说,大姐,那不是监狱,是临时拘留所。
不不不,她坚持说,是监狱呵,什么坏人都有,挤在一块儿了。
警察和监狱在不少群众的心中都是恐怖的场所。
那就监狱吧。
我想在小区门口把这只金黄金香蒲绒枕头给了那个中年女裁缝,没有见到她。
看来,难道她也被拘留了?
保安说,不拘留她,工作时间差,警察碰不上她,是暴雨,她没有出来。
我说,保安师傅,把这只枕头放你们这,她出来的时候,给了她,让她帮我去掉里面的内容四分之一,再缝好,我哪天碰到她,再拿,如何?
好呵。保安说。
保安是城市最下层的人,如兔子,谁都想欺负他们,我没有欺负过他们,也没有想过,因此,和保安说话就很亲切。
我有好多亲威的孩子们混在城市,打着最累的工,干着城市里最需要却最没有城市人愿意去做的活,我知道他们的心情,所以,我对他们总是怀着尊敬。
我和保安交流没有障碍。
我和城市里好多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人交流起来有不少障碍,我说过,我进化的程度不够,所以,总能够感觉到他们刺目的夺眼的逼人的自以为自己的确很是个人的目光。我在这种目光下,看到的反倒是一个人的卑下。可惜,我没有尼古拉斯·凯吉的目光,否则,我一定以一种忧郁的眼神向他们望。
这样说法也有问题。
我并不想树立敌人。
我不觉得人类的文明、世俗的城市和贵族的生活状态是一种耻辱。
我只是觉得有些人,特别是有些被物质异化之后的人,却是有些问题。可是,说他们有问题是不对的,因为,我的逻辑前提是他们是被物质异化之后的人,因此,就不应当作为一般正常的人看待。如果非要被异化的物质人正常地平等地看人,这对被异化的物质人是不公平的。
当然,其实,我们曾经都茹毛饮血。
把金黄金香蒲绒枕头交给了保安之后,连续三天暴雨。
我早出晚归,有时候,回到小区,雨早已停了,可惜,那中年女裁缝还没有出来。
后来,有一天中午,我又到买枕头的超市买东西。我们那儿的购物卡钱不多,但一次也买不完,不得不多次去买东西。
我再次看到超市卖的枕头。
呵呵。我大吃一惊。金黄金香蒲绒枕头,有高的,有低的,有饱不腾腾的,有瘪圪挤挤的,有肥的,有瘦的,太多了。
我就大笑。一个导购员也过来,陪着我一起笑。我笑弯了腰,仰着头笑,又笑歪了脖子。导购员也仰着头笑,又过来三个导购员,也一起仰着头笑,也笑弯了腰。
我笑完了,问她们,你们笑什么?她们都停住了,愣着神问,你笑什么?我说,我买了一只可笑的枕头。她们说,是呵,可笑呵。
我就问,怎么可笑?她们说,很可笑呵。我说,是这样,你看,这只很饱满吧。她们说,是呵,很饱满,很可笑呵。
我说,不是,不是因为很饱满很可笑。那是因为?导购员都睁着好奇的、探索的、与发现的大眼睛。
是因为很不饱满的,才很可笑。我说。
那有什么可笑的?她们问。
我瞪了她们一眼,说,你们不知道,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
我回到家。
希望碰到中年女裁缝,把我的枕头要回来,不用做了,到超市换一只就行了。
她没有出现。
又过了两天,周末,我终于抓住了她,我简直觉得她象个犯罪份子,我抓住她的时候那种兴奋的表情都溢出锅来了。
可找到你了。我说。有些找着党的感觉。
她说,她一直在呵。
没有让警察拘留?没有呵。
我说,我的枕头呢?她说,做好了,拿吧。
我说,清理了?她说,是的,按照要求,倒掉四分之一,质量真不错,还里面两层,这要多少钱呵枕头?
我哈哈大笑,说,好,多少钱?
看着给。
我给了她两元钱。
她很快乐。
我就抱了我的干瘦的金黄金香蒲绒枕头,走了。
我实在不想让她把我的枕头做了。
可是,她已经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