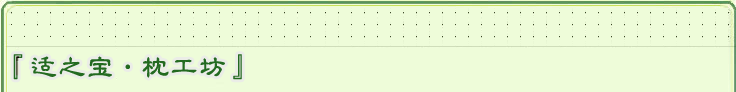枕头情人 ------
“宝贝,我用我生命中最绚烂的77天,做你的枕头情人。只当是一场为了分离的相遇吧……”
作者: 闵婕
窗外,雨一直下。闪电把夜撕开一条条惨白的口子,接着是一阵高过一阵的雷声。我抱紧怀里的香蒲绒枕头――这是谭乐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泪顺着眼角爬进丝丝缕缕的长发,凉凉的。原来,恐惧和死亡有着相同的温度。
雷宇走后,我就开始莫名地惧怕这样的雨夜。于是有了谭乐。
我和雷宇是大学同学,从大一时的牵手,到毕业后的同居,马拉松似的爱了八年。自从爸爸倾尽所有在北京给我们买了这套两居室,结婚也就提上日程了。我和雷宇的父母都不在北京,我们两个工作又忙,全仗我表妹岳月帮着张罗买这买那。岳月才二十岁,中专毕业好几年了,就在北京打工。工作三天两头的换,不是嫌累就是嫌钱少,人长得漂亮,习惯了男人请吃请喝的,日子倒也好混。
那天不知道怎么了,心口痛得厉害,经理看到我脸色惨白精神恍惚,特准了我半天假。
拿出钥匙,打开门,看到了雷宇的鞋子,还有一双女人的。卧室的门虚掩着,有沉重的喘息声传出来。我推开门的时候,看到一个赤裸的女人坐在雷宇身上。飞舞的长发让我眼前一阵眩晕。是表妹。
那一瞬间剧烈的疼痛让我倚着门框滑落下来。一起滑落的,是我坚守八年的爱情和貌似幸福的婚烟。
我和雷宇分手了。他从我的房子里搬了出去。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
我把床单,被子扯了下来,连同这个家里一切有雷宇味道的东西全都扔了。包括他的枕头--他唯一认可的适之宝荞麦壳枕头,因为他来自北方的青岛,多少年来就认可自己家乡这家富有传奇色彩的枕头专卖店,我睡过一次,由于睡起来有一点沙拉拉的响,不大习惯。
今年的北京,雨特别的多,和着电闪雷鸣,把黑夜渲染得格外的狰狞。雷宇,我的雷宇,他哀求我原谅他,我为什么那么决绝?我知道我在后悔,黑暗会让人丧失理智和尊严。我终于明白,八年了,他的味道已经渗进我的骨髓里。他一走,我的生活突然一片空白,就连墙上的钟也停了。我甚至在一个人的夜里无法入睡,常常蜷缩在新房的某个角落流泪到天亮。
我决定把另一间卧室租出去。我害怕自己在安静中枯萎。
谭乐打电话来的时候,天阴得厉害,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搬进来。
我说,现在。你能现在搬来最好。
三分钟后,门铃响了。开了门,一个俊朗的大男孩站在我面前。温暖的笑容如同午后的阳光。像雷宇,大学校园里的抱着吉他在我窗下唱歌的雷宇。
“请问,是这里有房间出租吗?”谭乐很有礼貌地问。
“是的。可是,是你住吗?你怎么这么快?你不要搬家吗?”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已经搬来了。”谭乐笑着指指背上的吉它和身后的皮箱,然后把身份证递给我,“我叫谭乐,大学毕业,刚到北京,社会关系简单,没有不良嗜好,只是会偶尔弹吉它,如果,你不怕吵的话,我想,应该没有别的问题了。”谭乐,1984年生,哈尔滨人。我忍不住笑了,“你没有租过房子吗?难道你都不要看看房间里的东西也不问问房东是做什么的吗?”“如果房东是你,我想,就不用问了。”谭乐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为什么呢?”“不为什么。”
雨下大了,我又看到了闪电。于是我关上了门。谭乐在门的里边。
那个晚上,我安安稳稳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同事说夜里又打雷了,我居然没有听到。
晚上回家的时候,谭乐正在布置房间,我过去看了看,简单,干净,床上横着一个大大的枕头----让我吃惊的是,居然也是适之宝枕头。不过不是那种我感觉有些原始的荞麦枕头,而是一个全部填细小蒲绒的那种枕头,上面还有一面绿色的叶子,看上去很舒服。谭乐说,差不多割160多棵蒲棒才能填满这样一个枕头,青岛住在水边的农民光要割这些蒲棒要2天时间。“蒲绒是带有天然香味的,很柔软,很舒适”,我当然知道,因为小时候,我的妈妈就使用这种枕头。
之后的日子安宁了许多。谭乐在酒吧驻唱,每天晚上十二点回来。回来就静静地呆在房间里写歌,时不时拨拨吉他。我也开始在榕树下网站写一些温暖的文字,生活渐渐充实起来。
雷宇离开整整一个月的那天,我发现,我怀孕了。谭乐回来的时候,我在客厅里喝酒,流了满脸地泪。看到他我努力地站起来,想躲进卫生间。可是就在擦肩而过时,我跌落在了他怀里。他抱起我走进卧室。当我抬起头,我看到了雷宇熟悉的脸,哭着说,“雷宇,我怀了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结婚吧,我们马上结婚,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没等他说什么,我就用唇封住了他全部的爱。他轻轻地把我放在床上,让我枕着他的肩膀,在他低沉的哼唱里入睡……“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是只能在梦里拥抱你……”
早上醒来的时候,头很晕,发现自己睡在谭乐怀里。恍恍惚惚地记起了前一天晚上的事,从脸一直到耳朵都像火烧似的。看着眼前这个小自己五岁的男人,有一种久违的温暖。
爬起来洗了澡,给罗兰打了个电话问她有什么建议。罗兰是我本科时的室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结婚两年了,现在挺着个肚子幸福地做着贵妇。罗兰说,“闵婕,婚姻不是儿戏。我只说两句话,第一,对男人不能一味的宽恕和纵容,第二,如果不能给孩子幸福和完整就不要慷慨地给他生命。”
其实,把电话给罗兰只是想听到她的支持。我不可以杀死我的孩子。绝不可以。罗兰的反不反对是她的事,我怎么决定是我的事。她只是给了一个建议。我这样安慰自己。
我没有告诉雷宇孩子的事。至于谭乐,家里的活他都抢着干,无论我做什么,他都说,“乖,你需要休息”。他开始固执地叫我“闵婕”而不是“闵姐”,当然,这一音之差并不能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任何变化。无论他叫我什么,他都只是一个孩子。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考虑如何把孩子留下来。结婚,或者干脆辞职。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这是我和雷宇的孩子。我已经失去了雷宇,我不想再失去孩子。
如果不是罗兰的死,我想,也许我真的会把孩子生下来的,或者我会回到雷宇身边也说不定。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原谅。甚至可以说,他自信他一定会得到我的原谅,他很清楚我八年的感情已经让我一生都无法摆脱他。我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女人。
收到罗兰的信是在一个星期之后,那时,她已经身在天堂。她的丈夫抛弃了她和她肚子里六个月大的孩子。两天前,她服了一百片安眠药又割了脉。一尸两命。她说,她离开这个世界,只是不想蓄积的仇恨让她忘记她们曾经怎样地深爱过。她说,做一个幸福的傀儡,她太累了,那是她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在罗兰的葬礼上我见到了她的宋旭。两年前的教堂里的誓词仿佛就在耳边,“宋旭先生,你愿意娶罗兰小姐为妻,不论贫富贵贱,不论健康疾病,都与她不离不弃,相守一世吗?”“我愿意”……罗兰是我们的班花,她曾经是一个美丽幸福的新娘,宋旭曾是他最大的骄傲。只是短短的两年,爱情就过期了吗?所谓至死不渝的爱情,难道两年就可以寿终正寝?!这个曾经发誓与罗兰执手携老的男人,短短两年里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丢下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妻子去另一个女人的石榴裙下寻找风花雪月了吗?!
我走到宋旭面前,直视了他一分钟,拳手捏得很紧,如果我是男人,我想,我肯定会揍他一顿。这个时候,有人拉开我。转身的瞬间,我的血液凝固了。是雷宇。他在向我微笑,努力地表达着一种和平。
我抬起手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只是下意识的反应。打完扭头就走,以掩饰自己夺眶而出的泪水。
这个时候,任何乞求都显得格外虚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感情的问题,也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得了的。男人已经太懂得如何去博得同情和原谅了,何必再去溺爱和纵容他们?!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谭乐正坐在阳台上唱歌,一路上有你……他知道我去参加葬礼,怕我回来难过,就没去上班,一直在家里等我。
“谭乐,陪我去喝酒吧。”“不行,你身体不好。”“这孩子我不要了。陪我去喝酒。听着,这是命令。”
从酒吧出来,我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我对一个小我五岁的男从哭诉自己荒唐的爱情,任由他心疼地把我抱在怀里我也不做一点反抗。
到家了。
在我关上卧室的门之前,谭乐已经有一只脚踏了进来。他粗暴地把我抵在墙角,又温柔地在我耳边念着我的名字,然后疯狂地亲吻我。我闭上了眼睛……
窗外,雨一直下。
黑暗中,我们紧紧抱着彼此。当他蜕尽我最后的屏障,我说,“雷宇,抱紧我,别走……”他突然离开了我的身体,把自己深深地埋进枕头里。
我把他抱在怀里,感觉得到他剧烈的颤抖。
那天晚上什么都没再发生。谭乐拥着我入睡,直到天明。他的胸膛宽阔而温暖,那是雷宇再也不能给我的感觉。
第二天,谭乐陪我去医院做了手术。不痛,只是睡了一觉。像是做了一个梦,无力挣扎无力苏醒的梦。直到邻床的女孩拉我的衣角,我才醒过来,已经不在手术室里了。她问我,“姐姐,你为什么哭了……”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我终于还是失去了我的孩子。尽管是在完全的昏迷中,我还是本能地心痛和流泪。
谭乐抱着我回了家,在那一个月里,他对我无微不至。唱歌给我听,褒汤给我喝,给我讲家里的冰雪,还有那些陈年的旧事。每天晚上他都会亲吻我的额头,用他纤瘦的手指抚摸我的长发,让我靠在他的肩头,在歌声中安然入睡……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
在一个有着明媚阳光的清晨,我醒来发现自己不在谭乐怀里。他的吉它和皮箱不见了。只留下他大大的蒲绒枕头和一句话。
“宝贝,我用我生命中最绚烂的77天,做你的枕头情人。只当是一场为了分离的相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