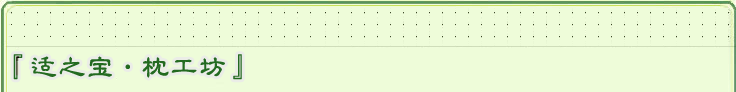妖魔化枕头
第一次被枕头的力量所征服是上中学的时候,看米国电影《超人》,男女主人公终于不能自拔地睡到一起了,我们看到的经过删减的镜头就只剩下第二天早晨两个人甜蜜地偎依在一起,深深地陷在两个庞然温暖而且暧昧的枕头中间。如此含蓄而且让人浮想联翩的枕头,顿时让我油然而生一种“人生得一枕头足矣,斯世当以手足视之”之热望。
在此之前,枕头于我只有一些破碎的记忆,不足道。最离奇的记忆是有一天妈妈午睡,随手抄过来一个小板凳垫在颈下,居然也可安然入梦——受这种教育的我不可能对枕头有刻骨之恋。
很多年以后,我以一个业余学者的身份发现一个真理,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宣传一个“克己复礼”的主旋律,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把一切都搞得不舒适,比如正襟危坐的太师椅之类——就这破玩意儿,还不是什么人都能坐上去的,因为坐上去是要体现威严的。推理之,所以枕头这东西也搞得硬梆梆的,就是不让你舒坦。但在床上如何克己复礼,睡觉的时候如何表现威严,对于我是个难题,无论怎么推演我都得不出一个高尚的结论。不过,既然我们把入了洞房做的好事说成“行周公之礼”,把一通乱搞的色情小说都可以上升到“肉蒲团”的高度,肯定还有专业人士做文化的“梳理工作”,我就不操这个心了。
相比之下,我更相信《笑林广记》,这里有一个笑话说,新娘子回门,有人打趣问,婆家与娘家有什么不同,这新娘子说在家里枕头放在脑袋下,婆家是枕头垫在屁股下。这种说法我很喜欢,因为古典枕头也有它灵光一现的时候。
虽说物尽其用,但我脑海中闪现的却是南宋“孩儿枕”之形状,据说这是中国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一想到硬梆梆的孩儿枕垫在身下,我就觉得这很不人性化。我在高中时曾经爱过一阵科学小发明,拜《笑林广记》和孩儿枕之启发,就想搞一个人形枕头出来,以我的性取向,这人形枕自然是美女题材的。当然,像所有凝聚了智慧和伟大创意的发明创造一样,它遭遇了无疾而终的结局。若干年后,我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糙老爷们,在他的独身公寓里,他的床上,摆着一个巨大的沙皮狗公仔,他说那是他的枕头。真变态。这样一想,即便我当初妙手回春巧夺天工,人形枕横空出世,我也会被妖魔化为一个变态狂想症患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无功而返是一件好事。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但美女枕头未能如愿,截至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享受到过超人的枕席之乐。这好象是一群和我同样爱科学的家伙搞的,他们把克己复礼置换成人体动力学,觉得颈椎这东西不能太纵容了,所以一定要严加管束,软中带硬什么的,软中带硬我不反对,但他们还舍不得往枕头里放更多的填充物,所以就是不舒服。
其实以我退化论的观点看,人类直立行走之后,那几块颈椎骨担负起支撑脑袋的艰巨任务,更糟糕的退化是人类大脑还越来越重,所以颈椎越发显得孱脆弱,所以晚上一定要用枕头找补回来。枕头不过是人类退化的一个标志而已,相对于其它动物来说,这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当然解决枕头问题的另一个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人类再接着退化下去,退化成ET的形状,我看那时枕头也就没什么用了。
本贴rascal |
rascal 文章是迄今为止 对于枕头文化和发展最为精彩的论述!
经典语言多多 例如: 枕头不过是人类退化的一个标志而已!
《枕头记》小编